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经济进入了失去贵金属约束的美元本位时代。信用货币体系下,美国成为全球货币政策的实际制定者。货币不再中性,美国不再收缩,美元霸权的全新模式开始驱动全球经济,整个世界都开始为绿纸片疯狂。美国的货币,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日本和西欧的技术,中东和俄罗斯的石油,全球的市场;各主体入局的时间虽然各不相同,但美国在这套模式中通过铸币权和技术开放的优势,始终居于食物链的顶端,并引领了“盎格鲁—萨克逊”经济体系的狂欢。这个所谓的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国际货币安排,而是一个动态的体系。以美元为首的国际货币从实体和金融两个维度加速了的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各主体要么作为生产者(日本、德国、然后是东南亚、中国和印度),要么作为消费者(美国、南欧、西欧),要么作为资源提供者(石油国、俄罗斯、巴西),都在这个体系构筑的食物链中生存。这就形成了三个世界的新全球产业格局。
市场主义的最大边界当然就是国际贸易和全球化,任何希望从中获益的经济体都必须服从全球市场化的“规则”,“与国际接轨”进而改造自己的市场、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社会和自己的思想,自由主义是其中最先被改造的那批。
但是全球化的现代形式具有自己最高的指挥官——美联储(原来是金本位,自动调节机制),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发展最高峰。全球化红利的最大受益者,纳入分工体系和美元体系。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及时加入了全球供应链,为什么出口导向会赢,并非是比较优势发挥了作用,而是这次融入世界的努力与美元体系下有效的消费国、生产国和资源国的全球分工相匹配,这既提供了巨大的终端需求,也获得了产业和技术的转移,这种转移的正的外部性特别明显,那就是——山寨机。
其实,中国在全球发达国家主导的产品内分工中,通过外包获得样品,然后反向工程,中国的关键不在于利用了比较优势,其关键优势在于它能够迅速而广泛地在全社会范围内传播与积累知识——即山寨化。现代科技和管理经验的引入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长期影响远远超过了比较优势所强调的范畴。巧妙的是这不仅仅是进口替代,很快,更加便宜的商品变为了出口导向,这是东亚胜出而拉丁失败的关键。乡镇企业改变了行业内的竞争格局,很快他们开始升级,请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把他们在MBA课程学的东西,进行了试验,无非就是治理去家族化,生产福特化和注重微笑曲线的两端,研发和营销,以及品牌建设。另外一方面,外来的竞争,优化了市场结构,改变了资源配置的参数和环境,产业内竞争结构变化,加上知识外溢,和人才(MBA教育),提升了TFP。
全球有13个经济体在连续2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保持了7%以上的GDP增长率,所有这些成功的案例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这绝非偶然。它们成功的核心部分就是利用了全球经济提供的知识、技术和需求。中国是其中增长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这种规模的增长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就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
漫长而屈辱的19世纪消磨了中国的原创能力和理论自信,全球化红利的本质在于,美国主导的生产国、消费国和资源国的分工,连接他们的就是储备货币的循环投放,加入 WTO加速了这一过程,WTO的规则更多涉及销售而不是生产,这样对中国的总成本领先策略是有帮助的。全球化不但提供了需求,还提供了要素包括技术和资本,最重要的是提供了制度,也就是与国际规则接轨,这就形成了传统计划体制外的市场平行世界,通过鲶鱼效应做增量改造,直到引发原来主流部分的体系性变化。
随着中国的入局,全球化3.0渐入高潮。但就算是中国幸运跟从了全球化潮流,那为什么中国增长如此之快呢?可能主要还是各种双轨制提供的利益空间,这是国家角度的总成本领先竞争策略,为了尽快完成经济起飞的原始积累。我们称之为“大推进”(big push)策略。同时政府以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或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生产、出口与投资,追求GDP高速增长的政策目标。这是一个国家意愿的上下结合的过程。三种力量在其实各自扮演合适自己的角色,共同推动神速增长。
首先是中央政府,这是战略层次,这本质上是国家能力的一个综合体现,现代国家能力也是也是一个马斯洛体系,从最基本的安全到最高级的全面发展存在着上升的阶梯结构。除了一般的法律秩序和政治稳定以外,这里同大推动策略最相关的部分,就是货币和资本,购买力决定需求,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在市场化初期也是自律的产物,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是提供符合经济增长和经济货币化所需要的信用货币投放。它既可以作为交易媒介膨胀,也可以作为要素(资本)膨胀。但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被动投放,他们都做得过于成功,长期实行宽松和放任的货币政策。这一方面体现在多年负的实际利率,成为铸币税的唯一享有者,而且通过货币供给推动的通货膨胀,形成隐蔽“税收”。政府的货币权力不断扩大,成为货币化的最大收益者和金融资源的最大经营者。另一方面就是汇率,这其实是总成本领先政策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最受竞争对手诟病的一环,国家重商主义或者新重商主义的源头。尤其是在1994年,在完成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的过程中,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一次性完成了近50%的贬值,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特别明显,从而使中国对外竞争力大幅提升,出口飞速增长。
战术层次上,地方政府是大推进战略具体的实施者。首先多数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大胆试验是其中的一项关键内容。本质上说地方政府是通过GDP锦标赛和争宠机制参与到增长过程中去的,处理地方和中央关系的1994分税制彻底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一方面,在税收方面使得激励相容。这导致政府行为企业化,一个地方政府相当于一个地方企业,一把手就是 CEO,可以想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工业园开发和招商引资。地方以税收、土地等优惠条件进行资本争夺,村村冒烟地形成了7000多个开发区或者工业园,更加高级的形态是形成产业集群,大量的重复和冗余投资,在提升总供给能力同时也形成了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1997年以后有了新的玩法。根据财政部数据,2010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收入增加到了2.9万亿元,相当于GDP的7.3%。2003-2008年中国政府征用了140万公顷的农业用地,转为城市用途。土地出让金其实是未来70年地租的一次性获得,目的是尽快获取土地收入,作为准备金,同时获得银行信贷,杠杆撬动,从而迅速推动基础建设进而经营城市,加速城市化。地方想象力更加丰富的是地方融资平台,它们从土地资本化延伸而来,是包装资产注入平台,作为资本金和抵押物,套取银行信用和更大的杠杆。
最后,增长意图的大部分力量释放是通过国企、央企和准国企(例如融资平台)来实现。一是硬件建设,包括大多数基础设施,例如铁路、公路、港口,通信。不可妖魔化这些投资,在人均资本拥有量不到发达国家1/10的落后情况下,应当说这些都是发展制造业和快速城市化所必要的投资。但效率总体上可能并非很高,特别是2009年执行“扩需求、保增长”的方针,4万亿元投资,10万亿元贷款,大部分都给了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政府所属的国有企业(“央企”)。在能源、原材料、交通、通信、金融等重要行业,中央所属企业建立了强大的垄断优势。国有企业依托占有公共资源和行政垄断地位获取了巨额利润,而这些利润又不需要向国家这个大股东分红,因而不能被运用到急需加强的公共服务领域,而是留在这些国有企业,由它们自行支配。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19870.6亿元,但是仅仅上缴440亿元红利。上缴收益占国有企业利润比重只有5%。大部分利润又被投入到大推进的诸多建设项目或者产能中去了。
这种三位一体的完美配合就形成了一个强力刺激总供给的大推动策略,特别是其中国有企业的作用,被索罗斯等冠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名号,因此不少人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新重商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体。某种意义上说,它抓住了一些现象和特征,但又似是而非。无论怎么称呼,它同国际资本主义(以美式大财团和跨国公司为代表)不仅仅是发展时间、发展阶段、发展形式和发展顺序方面的差异,而且是发展内涵和成果归属的问题,这才是试金石,当然没人否认其中改进的空间仍然是巨大的。
所以中国过去30年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本质上是——全球化3.0的中国镜像,即GDP锦标赛。这个判断里面有四重涵义:1)中国用的是准市场化的方法;2)全球化3.0是主要推动力,为什么不说市场化而说全球化呢?因为全球化包含了前者,是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市场化;3)竞赛首先是国家间的,是“赶英超美”和“民族复兴”,从1840年开始,中国人民就生活在某种紧急动员状态下,这是一场各大国之间的竞争;4)中国是个大国,国内地区间的竞争也是整体竞赛的基础所在。
因此,中国过去的30年发展道路是一个迎合了全球化3.0再分工、供应链再造和产业转移的市场化过程,这个过程由于全球各国之间和国内地方政府之间的GDP锦标赛机制得到了加速。整个改革开放历程,大致可以总结为市场化确定了激励机制和信号系统,这极大激发了民众的创富意识,半市场化要素垄断定价加速了资本积累和促进了国际竞争。聪明的政治家所做的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凝聚改革共识,发挥群众原创性,不阻碍试验,技巧更高的就是善于连打带消,并在关键时刻啃下硬骨头。在国家竞争的大背景下,相比其他西方经济体更加注重短期利益的政客体制,中国的政治体制安排更着眼于整体经济的成长,这无可厚非,特别是其中包括着帕累托即多数人都有所改进的状况。这究竟是决策者的高瞻远瞩,还是技术官僚的悉心安排,还是个体的获利动机,可能已经无从分解,它们通过市场和政府混合形式上演了一部宏大的交响曲。
无需讳言,速度优先的大推进策略在实现国家原始积累的这一阶段性目标方面功不可没,但后遗症也可谓众多,对内这可能是最大挖掘了中国的潜力,甚至在有些方面是破坏性的挖掘,从环境污染、贫富悬殊和垄断腐败方面的证据处处皆是。那么问题就来了,旧常态被打破以后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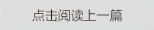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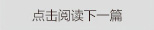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