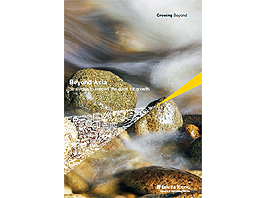钱德兰·奈尔|文
从现在到2050年,世界人口预计将从67亿上升到90亿,同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过上美国人那样的生活。
——托马斯·弗里德曼
大约20年前,我发现自己在各种企业和论坛作演讲时会越来越多地提到环境问题。它与各种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以及政治问题之间的联系是大家反复讨论的话题。久而久之,我发现自己日渐被一个问题所吸引—如果亚洲继续沿着西方的道路发展,结果到底会怎样?尤其是对于如此广大而又特殊的地区而言,如果每个国家都把消费驱动型社会当成自己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那将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我对此非常着迷。
我常常会调整自己的观点,在许多问题上生怕自己会被指责不具备发言权。但随着演讲机会的增多,我对自己许多尚不成熟的想法进行的检验也越来越多,从中可以看出人们是如何接受我的想法的。
我发现有一部分听众,特别是企业领袖和政策制定者,他们似乎对我所提出的认为目前的发展轨迹不具可持续性的观点感到不安。但也有一些听众会表现出广泛接受的态度,尽管有更多支持性的评论是在会后私下提出来的。
我感到很好奇。到底是哪些位高权重的人士可以决定哪些话题可以接受,哪些观点可以表达?我还能表达更多意见吗?
当然,随着越来越多论坛的召开,我表达观点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这些论坛所讨论的许多议题都是我所熟悉的,因为我在相关领域从事了很长时间的实践研究,做过首席执行官,做过环境咨询师,管理的项目遍布亚洲—从中国和印度到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
为了不冒犯别人,我竭尽所能做到礼貌和谦卑,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被无端地指责为消极悲观分子。对此我实在难以接受,因为事实上长期以来,我都认为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有一次在瑞典的一个论坛上,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对我说,我其实是个煽动者。尽管这只是友好的调侃,但我能察觉出,虽然他同意我大部分的话,就像很多联合国官员一样,可他还是担心我可能已经触碰到一些潜协议。因为我所抛出的挑战,让包括企业领袖、政治家、学者等在内的听众都始料未及。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香港召开的一次区域经济峰会上,我的言论使我显然被归为了“环境学家”一派。我谈到了大珠江三角洲地区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的问题,对投资增长造就繁荣、环境也会受到繁荣回馈这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对此,很多人表示赞赏,但同时也认为我是杞人忧天;环境不会变得像我所说的那么不堪,因为在那之前,企业便会承担起责任。
15年过去了,香港的污染越来越严重,与它的邻居广东成了一对难兄难弟,会议的议题也变得更加宽泛—从探讨如何与环境更好地相处,到关注全球气候变化。
然而, 2008年在美国召开的一次讨论会却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复。尽管与会人员大多为自由群体,但我对于美国人应当重视全球变暖问题并应该采取行动的建议,却并未得到广泛接受。显然,即便只是传播消费可控的言论—例如建议将车辆拥有量限制为每个家庭一部、引进碳关税,或者哪怕只是少吃点儿—都等于干涉了美国内政。
尽管如此,随着气候变化逐渐进入各国的政治议程,逐渐成为主流议题,我发现自己的言论遭到的直接抵触变少了。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日隆,同时越来越多的论坛也为许多鼓舞人心的演讲者提供了更多的空间,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向听众宣传生态居民的责任,让他们“改变自己”。领导力依旧,但只有在它注意到有新的社会网络能够动员民众采取行动的时候才会发挥作用。“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取代了技术革新,消费者变得更道德,而企业被强烈要求减少环境足迹,因为“逐绿”意味着省钱—同时还有益于世界,有益于消费者,有益于它们自己和它们的股东。
不管怎么样,至少问题正逐渐得到重视。人们的态度也慢慢地—有点儿太慢了—开始改变。2009年7月,我在巴厘岛进行了一次演讲,演讲的对象是一家全球老字号私人财富银行的客户。演讲中我重点谈到了消费导向型增长给亚洲带来的难题。他们表现出来的兴趣让我颇感意外,有些人甚至对我只是随口而说的话表示接受,例如“珠光宝气已过时”、“少就是多”以及要限制消费等。听众当中有一位全球领先的出版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本来期待能与他单独共进晚餐,但听完他的一些建议后,我觉得应该先把自己的演讲延伸一下并写下来。你们现在读到的正是我们谈话的成果。
既不东,也不西
各位需要花一些时间去了解这本书的结构。该书的核心部分是讨论作为一股经济力量而重新崛起的亚洲,及其给自身和世界造成的困境。但在我与一些朋友分享了一些暂定的纲要之后,他们常常提醒我,要确保我所说的话不会被视为反西方言论而遭到攻击或排挤。
坦白说,这种告诫让我感到困扰。为什么他们一方面赞同我去传播自己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有必要提醒我警惕那些世俗精英们的反应呢?呼吁人们去关注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难道真有那么危险吗?要知道,中国和印度有不少主要的国际性刊物,几乎每天都会在其社评专栏刊登相关评论文章,而批评其他亚洲国家运作的文章同样随处可见。
不管怎样,我觉得还是需要澄清一下,这本书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攻击西方。它既不是说西方如何让事情变糟,也不是说亚洲怎么能让情况变好。当然更不是为了宣扬什么“亚洲时代”的来临,西方必须接受新的游戏规则等等诸如此类的观点。然而有越来越多的评论者,其中不乏亚洲人,都纷纷加入到这种言论阵营当中。在我看来,这些言论的观点都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说这本书确实有某种攻击性,我想大多是针对亚洲目前所采取的发展道路。尽管有大量事实证明许多做法对亚洲各国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但各国领导者们在对待自然的决策上依然缺乏反思。
但无论如何,这本书是欢迎一些新规则的。这并不是说西方国家缺乏责任感。在欧洲和美国,有许多人都批评政府,指责它们未能通过实际行动兑现那些辞藻华丽的诺言,不论是提供发展援助、改善气候变化,还是进行全球化的军事行动。许多这样那样的压力并没有得到缓解,尽管后果可能没那么快到来。但西方国家该如何去做,并不是我要讨论的中心。相反,亚洲社会必须做什么,最关键的是亚洲政府必须做什么,才是本书关注的焦点。
我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亚洲必须作出改变,同时我也越来越不解,为什么那么多亚洲企业的领导者几乎从来不对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管理倒退等问题提出任何看法。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人,在公认的世界顶尖大学和商学院中接受过教育,为什么他们要选择保持缄默?难道他们真的是忙到连稍微思考一下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吗?还是说,他们真的觉得其实没有任何问题?真的觉得什么代价都只是短期的,繁荣最终还是会逐步实现的?
于是我开始猜测,他们也许只是太害怕而不敢说出来,害怕说出来后,不知道他们的企业或商业伙伴会如何看待自己。我尝试着逐渐深入地去了解他们,常常去听他们的“绿色演讲”。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确信,尽管他们都有着强大的实力,他们还是会害怕面对理直气壮的理性,但在私下除外。我怀疑,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保持沉默的原因只是不愿意越线。不管有什么矛盾,这个体制毕竟还是给他们带来过不少福音。拿供应链管理来说,它能帮助企业以便捷的方式将一些有害的外部因素(例如污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哈佛商学院模式的供应链管理,在国际上极具专业认可度,作为多国委员会的亚洲代表,如果能把自己提升至这种专业水平,那将会得到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这么说来,质疑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事实上,还有一些别的因素在起作用。我注意到许多世界级的精英商学院(绝大多数在美国),开始用越来越多的方式去塑造亚洲学生的思维。在我看来,这些年轻人包括一些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并没能在这些学校里学到那些能让他们变得更好、更富有责任心,能够为自己祖国所遇到的问题出一份力的实用技能,学校更多的只是传授意识形态。
在这些学校的教学当中,丝毫没有提及人们应该如何在对地球施以限制和约束下进行管理和创新。相反,这些学生被教导的是,依靠自由市场的帮助,消费驱动型经济已经成为实现繁荣的最佳手段。政府也在其中起一定作用,但主要是充当为消费驱动型经济扫清障碍的角色。而民主的加入更是为其锦上添花,西方世界不仅成功地推进了文明进程,达到了幸福和科学成就的新高度,同时还—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观察到的—来到了历史的终点。
一般来说,这样的自恃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跌跟头。然而,时至今日,这种观点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人们对它竟然还保持着相当的自信,这着实让我感到诧异。我在一所工商管理学院任教,学生大多数来自亚洲,也有一部分来自欧美国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接受过西方教育。然而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极少数人会对作为他们工作和生活基础的种种假设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完全没有必要。即使在今天,尽管他们的祖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中大部分人仍然会贬低自己的出身,并把自己的远大抱负选定为进入投资银行或跨国企业。他们其实很聪明,非常聪明,但在心智上却很不成熟。
京ICP证090880号 京ICP备10026701号-8 |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京第01015号 |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第直10001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京第01015号 |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第直100013号Copyright 财新网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复制必究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涉网络暴力有害信息举报、未成年人举报、谣言信息):010-85905050 举报邮箱:laixin@caixin.com